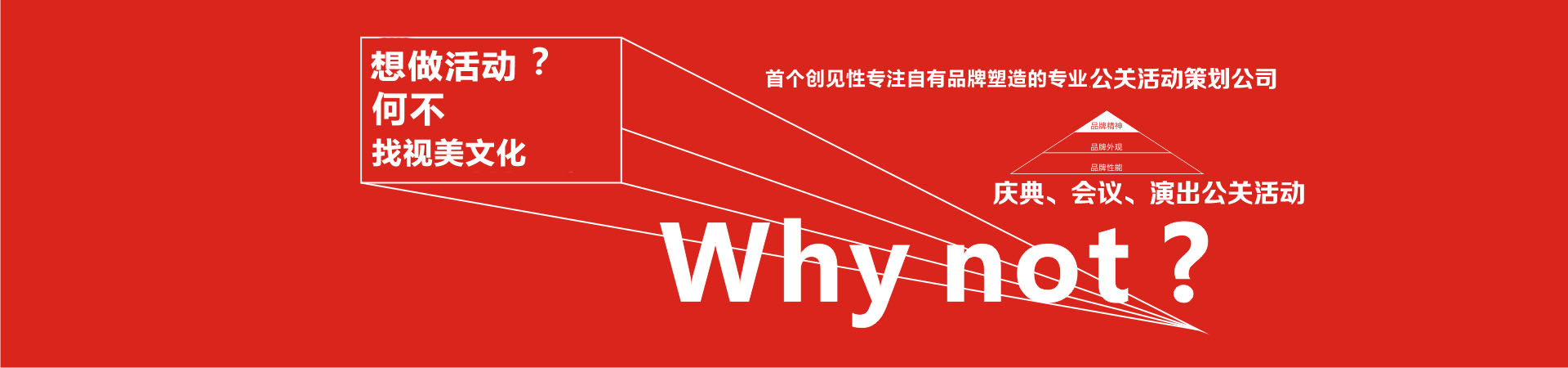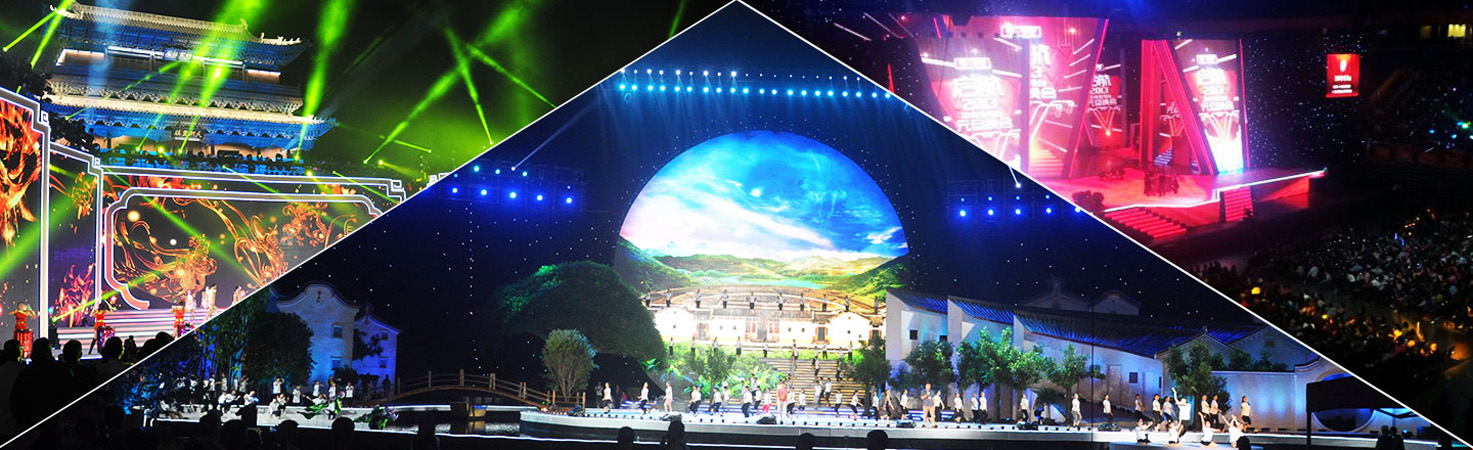8月3日7日,蟒国剧团作品《失忆症蟒国》将在北京正乙祠古戏楼演出。舞美设计以剧场建筑为依据,根据剧本风格,做出了在传统戏楼中设计当代话剧的尝试。进行核心道具的设计与制作时,设计师分别对全剧上下两部分以装置艺术和工艺美术的标准进行工作,追求作品质量。本文即是剧团舞美设计对于创作的思考与梳理。
接触到《失忆症》的构思创作准确的说其实可以将时间定位到去年九月末,当时因为很多客观的限制条件所以关于《失忆症》的舞美构思没有得到好的延展,今年重排《失忆症》视觉构思得到了更大的释放空间。今年参加大理的CORAT艺术现场我们《失忆症》得到的演出空间是坐落于喜洲古镇北洋时期军阀的旧宅大院,大院的建筑结构为传统的白族“三坊一照壁”的样式。正方朝南,面对照壁,三坊每坊皆三间两层,整个建筑皆为木质结构。照壁和地面为石质。所以我在考虑文本视觉化走向的同时还要照顾到“半开放式野外演出剧场的特性,”就像是日本利贺戏剧村里的合掌造一样,日本的戏剧开拓者将原来属于民居性质的木屋改造成了剧场,这样的剧场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因为之前有人居住过,所以整个建筑的“呼吸节奏”是与人的呼吸方式吻合的,演出空间内存留着大量的人的身体记忆,这样的身体记忆会让走进剧场的观众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相比合掌造而言,喜洲的旧宅大院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正方与两侧厢房三面围合在上方形成了一个天井,天井原来的用途是采光、通风、排雨水,这给舞美的设置和现场的合成会带来一些麻烦,采光会影响到对光时间,露天会增加意外天气对演出效果影响。但这些限制条件本身又有它的长处一面,“三坊一照”的结构加上露天的天井可以更好达到演员无麦表演时声音的拢音效果。露天的天井虽然在下雨时会影响到观众的观看的外部感受,但稀稀拉拉雨滴恰恰也和《失忆症》中从几百年的荒凉大旱过度到的大雨滂沱的时间相吻,无形中增加了观众内在的对文本的一种感官体验。
从喜洲旧宅到北京正乙祠古戏楼的转变,有一个空间属性的衔接点就是正乙祠原本也并非戏台而为古庙,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同为二层全木质结构,演员都需要在无麦的情况下表演。在《失忆症》道具设计方向上,我参照了古亭选址的要素,计成在《園冶》一书中,对古亭选址有过总结:“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斯園林而得致者。惟榭袛隐花间,亭湖拘水际,通泉竹里,按景山巓,或翠筠茂密之阿。这里提到的“花间”、“水际”、“竹里”、“山巓”等,都是经过人为选择后的“自然景观”,所以在全木质的建筑中设置舞美效果首选一定是遵循着贴近“景”的原则来实施的。
因此在设计《失忆症》中的主要背景道具灯时,我首先从“花、水、竹、山”里去寻找突破口,在从文本中提取到由干旱到大雨磅礴的极端转换,会让我联想到常规生命被摧毁的残酷景象,死亡的直观感受就是一个已经风化又长满苔藓的大象头骨,经过不知道多久风吹日晒头骨已经和山石融为了一体,从头骨山石上生长出的红色植物正代表着环境极度转换下的血色物种,这也正与血统高贵的美丽少爷家族吸食人血有一个很好地对应。
在对另一个道具伞的设计上我开始做了很多伞的资料搜集工作,作为少爷家族的一个传世遗物,从伞的款型选择上我并没有从现代的伞具着手,而是从更具时代色彩的油布伞切入,油布伞表面的漆皮效果同样让我联想到某种生命的附着与衍生,同样出于吸血家族的重要道具,将吸血蝙蝠的肢体结构融进雨伞也是文本转化为视觉呈现的关键步骤。
正乙祠戏楼不仅保留着原有的纯木质结构,而且经过后期修缮恢复了木雕花罩和雕梁画栋。当我们选择正乙祠作为《失忆症.蟒国》的演出场地时,不光对导表演的能力进行了一次大考验,而且对视觉部门提出了巨大的难题,困难在于本身正乙祠内部结构因为在清时期由庙宇改为戏台,清相比宋以来的建筑造型有了很大的改变,柔和的建筑轮廓、粗大的斗拱与柱身、檐柱的生起与侧角逐渐退化,换来的是更加繁复的建筑结构的细部装饰。这种在本以精致的结构上粉饰繁复图案的传统戏楼在现代灯光的呼应下显得极度奢华与精致。在这样的空间里想要增加视觉的筹码本身就并非易事,何况由于正乙祠是北京唯一还保存基本完好的纯木质古戏楼,所以对他的爱护可能要超过对现代的任何一个剧场。值得庆幸的是,《蟒国》描绘的是一个漫天彩云、虚空遍开百花的世界,剧作意向与舞台视觉张扬华丽、表演要求细腻复杂,这正与剧场里繁复的雕梁画栋不谋而合。
在《失忆症》和《蟒国》两个故事的转化中,我在将原来守旧的位置改成了便于更换抽拉的软景幕布,在纹案的选择上更多的考量上不仅要兼顾画风与剧场原有图案的协调又要明确的区分《失忆症》与《蟒国》在文本转化到视觉气质上的迥然不同,在检场和乐池的区域设置景片装置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流动架等舞台机械装置对古戏楼原有视觉的破坏。在主要道具弓和乐器的设计中,以流线为主,采用了花与蛇为主要元素的组合方式,与文本娇艳妩媚的蟒国大将军人物设定、华丽且以花朵刺绣为主的服装相吻合。